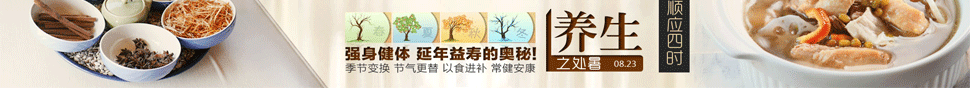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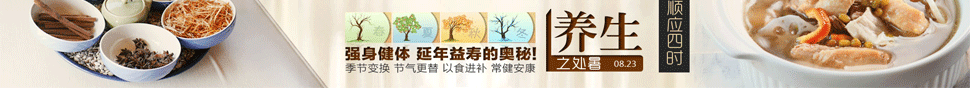
怀念陕北
本文作者:冯涛
引言
从13年前说起。
一个小道消息,犹如一声惊雷,爆炸在采油一处各个基层单位。有些职工议论着、彷徨着、忧虑着、观望着;有些职工说小道消息,不足可信,还是好好工作吧;个别职工忙着回家照顾80多岁的老人,没有时间议论此事。
然而,接下来的官方发文,证实了消息的可靠性。
一、撤离陕北转战陇东
“原采油一处转型,转战陇东,开发合水油田”。上级领导来我们单位,传达了上级决策,要求职工响应号召,做好转战陇东的思想准备。一下子,职工们懵了,他们走南闯北,有些先后在玉门、新疆等油田工作,最后为了延安安塞油田的发展,多次搬家来到这里,几十年大开发不懈奋斗,最终在延安建立家园,孩子在这里上学,老人在这里养老,和谐的环境,一片欣欣向荣的油田发展势头,他们努力着,开发者,为了这块热土,奉献着他们的青春和汗水。怎能说走就走,一排排的住宅小区、一片片的绿树青草、惬意的休闲场所、耕耘多年的油井、数年办公的场所、如亲人般让人留恋。还有在困难时期互帮互助的朋友,怎能就此割舍?延安安塞油田啊,难道我们就这样无情地走了?眼泪似断线珍珠,表达着心中的依恋……
上级领导多次动员,这是形势的需要,也是科学调研决策,我们几千人,几十个单位,非去不可。不得已,我们学习文件,跟领导谈心,转行业务学习,一系列的节奏,在上级的指引下,我们走着、观望着。然而,心里不是滋味啊,竟然解散了30多年的井下施工队伍。像这样整体解散一个专业,对于快退休的师傅来说,这是他们奉献一生的老本行,有的几乎哭了。他们对这次整体转行有着太多的忧虑和气愤,这是石油人对石油的情结呀。
转型学习了几个月,终归,几千人相继转岗了。他们有的老婆留在了延安,有的老公留在了延安,有的老人留在了延安,能完整留下一个家的,只是个别。自此,我们这些石油人,在延安和陇东两地跑着。一边是工作,一边是亲人。思念与忧愁,也分了两半,自此缠绵的心,跳动在两个地方。
二、初到陕北深扎油田
点燃延安牌香烟,我想起了初到延安的情形。
那是年8月,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着,外面是树林、平原、高山、河流……汽车跑了近6个小时,还在继续。同学们都在问陕北的安塞油田到底在哪里?难道我们要到“新疆的克拉玛依油田"吗?这么远啊!我们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,同学们都在车上睡着了。忽然老师喊下车,我们迷迷糊糊地蜂拥而下,以为这么出名的安塞油田,一定是高大上的,但是到了之后,我们失望了。
陕北的山,比我老家的还高还荒,还尘土飞扬。大人小孩的脸蛋,都有两个红晕,被称为“红二团”,说是延安“老红军”的孩子。后来才知道,是环境气候的缘故,风头高,又寒冷,吹红了脸蛋。
我们在一个叫高沟口的村里下了车,接我们的领导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单位,院子里有两栋楼房,墙面残破。难道,这就是延安安塞油田?有名的长庆有田?那一夜,我失眠了,想了好多好多。我的好多同学都哭了,尤其女同学。
第2天,单位领导给我们讲了李四光和铁人王进喜的故事,以及中国贫油论的故事。一周内,学习了单位的安全、技能、人事等规章制度。又一周后,同学们都分在了最基层的小站或小队,半年实习期,一月都很难见一次面。自此,我的生活和人生,在陕北延安的长庆安塞油田,拉开了我个人的故事……
陕北的冬天来得格外早,枯萎的树枝,随着冷冽的寒风摇摆着,发出阵阵清冷而凄凉的呜呜声。
一天早上,下了厚厚的一层雪,这可让我们高兴坏了。我们是油田井下作业,下雪路滑上不了山,只能在单位休息,这是老天给我们放假了。平时忙于修井作业,很少有白天的休息娱乐时间。那天上午我睡了很美的觉,做了好美的梦,和同学们在母校的操场上踢足球、打羽毛球,互相逗溜着,好不惬意。
中午,班长神秘地通知我们8个班员,到一个饭馆“开会”,我很纳闷,开会怎么放在饭馆?几个老师傅笑我傻,我因此成了他们开心果,也因此我的那些师傅一直很照顾我。原来,下雪是喝酒的日子,我们班聚餐,大家喝了好多酒,师傅都醉了,我因为第一次喝酒,也大醉,被师傅们背回单位,听他们说我酒后吐了好多,关于我酒醉的事情,师傅们说着,乐着。
三、陕北酒文化
说起陕北,必须说酒。大碗吃肉,大碗喝酒,是这里的风俗。客人或亲朋来了,陕北人的招待是诚意的,让你吃个够,喝个痛快,实实在在,不玩虚套,我第一次被这里的人感动着,尊敬着。慢慢地,我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和想法,融入了陕北这个大家庭中。我的班长是陕北人,厚道豪爽,给我手把手教会了职业技能,也教会我为人处世等好多做人道理,现在想起来,很是感激。如今,他退休十几年了,回老家养老,不知他可好,我很怀念他。
酒文化,是陕北最大的文化,不论农村、单位过事情或贺礼,都得满上酒杯,大家划拳或摇骰子或梦幻等,好不热闹。凡在油田上工作的,基本都喝酒,一是地方文化熏陶,二是油田艰苦环境喝酒提神。酒在陕北和油田,是大家工作学习、过节之余的最好的润滑剂,拉近了感情,也快乐了人生。
自此,思家了,疲累了,委屈了,高兴了,我们就喝酒。为此,我吟诗一首。
石油人的人生,
是一部发展的历史,
记录着奋斗和心酸的历程。
专一向上的石油人,
孤独的心声,
谁能读懂?
与大山结伴,大山给了石油人安逸,
与油井为伍,亲人给了油人的牵挂。
有了你们,
我们不孤独,
而你,一定很幸福,悦乐自在。
你可思念石油人?
四、陕北庙会
每年的3至5月份,陕北春暖花开,春和景明。沐着微微春风,吹着轻轻口哨,踏青在陕北的羊肠小道上,花香沁人心脾。此时,庙会处处可见,令人记忆尤深。
4月8日,延安清凉山的庙会,规模空前。由专门的会长主持,各地都有分会长。方圆几百公里,都有专门来虔诚拜佛的人,他们或磕头、或布施、或还愿、或祈祷、或敬仰、或求平安等,目的只有一个,都希望自己的愿望都能实现。人来人往,好不热闹。庙会也拉动了当地经济:特色小吃举不胜举,子长县的煎饼,延安的羊蹄等。还有摆地摊卖小东西的,如绥德县盛产的狮娃、安塞的腰鼓等。庙会养育了一方人,他们努力工作着,生活着。庙会每次都请唱大戏、陕北说书、音乐晚会。年轻人爱看晚会,中年人爱听说书,老年人爱听大戏。
我喜欢秦腔,所以在逛庙会的时候,一般在看戏和听戏。从小在我甘肃老家,受父亲影响,是个戏迷,也懂戏。例如《三滴血》、《周仁回府》、《杨家将》等,每次看着苦戏,听着哭腔,不由潸然泪下,为古人的忠孝仁义所感动。所以每年庙会的秦腔,我一定都会去看,哪怕工作再辛苦,生活再不如意。古戏今唱,唱的是哲理、公理、良善等,值得我们品味和学习。赶着庙会,坐板凳吃着凉粉、站立“吸"着羊蹄,听着陕北说书,真的是赛神仙。
看戏回单位迟到了,被领导骂几声,我也乐呵呵的,只当是庙会的戏剧和陕北说书。“叫声领导莫生气,听我把苦事表一番,我家住庄浪小家园,我读书工作在延安”……我的唱腔逗笑了领导,他还夸我唱得精彩。叫我改天领他去赶庙会,以后我和领导在一起,白天使劲工作,晚上使劲看戏,和领导在一起探讨工作和戏剧,乐在其中。
五、陕北信天游
陕北的信天游,豪放、凄楚、悲愤、抒情、传情,不论老少都能哼唱几句。尤其陕北红白喜事,都要请专门的音乐团队来助兴捧场。这时,信天游便是主角,听着让你泪流,让你神往。
这里“娶人"(结婚),别有一番情趣。长长的唢呐队伍,亮亮的笛音,畅畅的快乐,直至把新娘领进窑洞。唢呐手摇头晃脑、无比陶醉,仿佛比新郎还要高兴,一会儿唢呐朝天、一会儿向地、一会儿左右,故意吹着与喜事背离的调子,逗得大家哈哈大笑,增添了几分乐趣。“大红果子剥皮皮,人人都说我和你,本来咱二人没关系,好人担了些赖名誉"。既然没有关系,怎能结婚?
陕北信天游,对爱情的专一唱得很深情:“你没有婆姨呀,我没汉;咱俩捆成一嘟噜蒜,呼儿嗨哟;土里生来土里烂”。真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乡土爱情,白发落土,烂在尘埃。由此可见陕北人的纯洁和追求是勇往直前的。
延安成就了红色政权,也成长和发扬光大了信天游,一代又一代,传唱着,讴歌着延安的大发展。当然,也忘不了毛主席,他当年在延安“上朝”主政了13年。
山丹丹(的那个)开花(呦)红艳艳,
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……
六、老石油的故事
我在陕北时,师傅们的油田敬业精神,我记忆犹新。我参加工作时,大部分师傅都是50多岁的老石油了,他们是年兰州军区转业的军人。在油田已经奋斗和开发了20多年。他们大多家在农村,很是艰苦。我有个师傅,他有一位老人两个弟弟及三个孩子,全靠师傅微博的工资养活。他要供孩子上学,给弟弟娶媳妇,赡养重病的老人,每月的工资基本都花完了。他极其节俭,从不到饭馆或商场花钱,穿的衣服都是单位发的工作服。当时,我们几个年轻人看不惯,老说师傅寒酸。后来有天和师傅喝酒,他说:他父亲去世早,家庭困难,靠母亲养活了一家几口人,他是兄长,长兄如父,给弟弟找媳妇,是他的一块心病,再说老娘快80岁了,身体多病,每次给老家给钱,总要和老婆吵嘴打架……说着说着,他就哭了,很伤心。老师傅参加工作几十年,为油田发展奉献了一生精力。他工作认真,岗位每一个操作流程和标准,他手把手教给我们,每一次班组学习,他的笔记记录最完整最认真。他开玩笑说,把它传给“油3代"。老师傅的言传身教,一直激励着我工作学习,不敢懈怠。我老丈人是老石油,工作了一辈子,过节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,他讲他的石油故事,令我感动,时时向他敬酒,向老一辈油人致敬。他们的默默奉献和开发,才奠定了横跨5省的全国第一大油田——长庆油田。
当然,我们这一辈,是油田的主力军,算“油2代”吧。从我参加工作到现在,油田经历了大开发(--年)、大转型(-年)、大重组(至今)阶段。我们这一代经历颇丰富,而且为油田的发展,全身心地奉献着。“油田卫士”陈小军、罗玉娥等为了保卫石油,维护油区的安宁和稳定,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,还有很多很多,为油田牺牲的同志,让我们再次向他们致敬,我们油田最可爱的人,油田不会忘记你们。多工作,多学习,多孝敬老人,多培养孩子,是我们“油2代”人的责任,当然了,还要注意锻炼身体。
七、会战陕北
陕北的冬天,格外的冷。寒风劲足,直刺脸面。和往日一样,我们出去野外作业。值班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盘绕着,一会上了这山峁,一会又下了那山头,车窗外尘土飞扬,和着落叶风沙,风旋转着,吼叫着,几乎挡住和模糊了司机视线。这样的日子,我们已习以为常。
一个小时后,到了野外施工的目的地——XXX井,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抽汲诱喷,即把井里液体抽到地面,井里压力小于地层压力,达到地层油流进入井里喷射出来,这是措施作业中重要的一环。若果能抽汲出液体,说明措施效果良好,否则有待评价。我当时是技术员,压力很大,一方面要收集资料,核对数据,一方面是跟班干部,要操心井场安全等工作。作业到上午11点多,忽然一声巨响,山崩海裂般噗嗤声声刺响,一股黑风吹着石油液体,到处乱飞,覆盖了井场上空,我的第一感觉是井喷了。正想着要采取措施,忽听班长大喊:注意安全,撤离现场!我们都跑到了井场外,安全撤离了现场后才反应过来,井喷得厉害,将井内油管打成麻花状后喷出落在地上。一位快退休的师傅说,这样厉害的井喷,他是第一次见,若伤着人,后果可怕。我和班长商量,我下山向大队领导汇报,班长留守准备关井和采取措施。值班车下不了山,因为喷出的原油有10厘米厚,将路、车“埋”在里面,我只好步行去队部汇报。走了大约2个小时,踏着羊肠小道,脚被磨破了,脸被风刀割,又冷又饿,几乎撑不住了。
终于到了队部,我向总工程师和大队领导汇报了井喷。当听到抽汲诱喷成功时,领导笑得很开心,显露出对自己组织、设计、施工、效果的认可和对我工作的认可。当我说出原油喷出满井场、油管喷至地面时,总工程师笑容消失了,嘴角颤抖着,近视眼镜下的小眼睛皱成几道线,嘴里喃喃着埋怨我,大队领导也脸色阴沉,嘴里嘟囔着要罚我工资,撤销我的技术员职位。
最后,在大队领导的精心组织下,回收了原油,打扫了井场,并向上级工艺部门及上面大领导层层回报。我压力很大,闯了乱子,也做好了检查、降薪、撤职的心理准备。
过了几天,来了十几个专家,勘察了井位,详细调阅了该井的详细资料后,他们高兴地走了,并表扬了大队领导。
又过了几个月,专家进行了“会诊”,肯定了这片区块的开采价值。在以后的数个月,在这个井的周围,部井位了好几口,钻井声声,钻着油井。我的一颗心也放下了,工资没降,检查没写,领导也没再找我谈话。后来,听说上级给大队总工程师进行了奖励和荣誉证书。
有一天下着雪,很冷。总工程师把我叫到办公室:“当时说降你工资,撤你职务,让你写检查,是随便说的,你别介意。你组织施工的这口油井是评价井,有参考价值。好好干吧,小伙子,前途无量哦"。他嘿嘿笑着,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这位工程师,现在已退休多年,快70岁了吧,好久不见,还有点怀念。
八、陕北和石油文化
陕北的文化,很是繁荣。他们对文艺艺术,甚是推崇。陕北过年,很热闹。尤其是红红火火的大秧歌,气势豪迈的腰鼓,都必须表演。每年到腊月二十以后,各个单位或村镇,都紧张地进行练习和彩排,从正月初三到正月十六,基本每天表演。一家比着一家,从不落后。
农村的社火,到每家每户去表演,主人放一串鞭炮,给大家发一支烟,有钱的人,直接端盘上钱。锣鼓喧天,唢呐声声,热闹非凡。整个村子沉浸在春节的喜庆幸福中。社火多样:有《西游记》中的《三打白骨精》,玄奘师徒的装扮惟妙惟肖,有《白蛇传》中白娘子和法海斗法,白娘子怀孕斗法海,让人同情,有《三国演义》中的《桃园三结义》,人们为忠义的武神关羽感动着……很多很多。
我们石油单位,也组织了大秧歌队伍,演员以退休的大叔大妈为主,在正月十五,给机关或驻后勤单位表演,领导们很大方,表演完毕就给带队的秧歌头头发红包。大叔大妈们笑着、扭着、摇着,一派祥和喜庆。他们还在正月十五延安市组织的社火表演中大展演技,获奖不少,给我们石油人争了光,为石油的发展摇旗呐喊。单位还成立了《黑石油》等文艺团,常常下基层给一线石油人表演节目。也请陕西戏剧研究院秦腔演员,给职工们唱秦腔。请的有陕西四大名旦之一的李梅,名角丁良生、李爱琴等。演唱《三滴血》《周仁回府》《放饭》等,一些老人坐在台下,认真地看着听着,为戏里的苦情流泪,感动。谚语:“看戏为古人流泪,瞎操心"一点不假。
文化生活的大繁荣,与时俱进的和谐大氛围,营造和激发了石油人在艰苦环境下的奋斗精神。石油人干累了,哼一曲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的豪迈歌曲,浑身得劲,斗志昂扬地工作着。我自豪我是石油人,为石油努力工作拼搏。然而我们石油人的艰辛、孤单、疾苦、劳累,又有谁懂得和理解?
九、几回回梦里回延安
弹指一挥间,到合水油田工作,快13年了。13年啊,我想延安一定有大变化吧。那些油井还源源不断地出油吗?那些师傅们还健在吗?那个曾经我住过的小区还生机盎然吧?
“几回回梦里回延安,双手搂定宝塔山。”我想起诗人贺敬之的《回延安》,也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来,泪水模糊了双眼。
如今,我在转战的新地方——合水油田工作着,奋斗着,一刻也不停歇,快50岁的我,深深地感受到工作的责任和生活的重担。
十、怀念的泪水
就此收尾吧,说多了都是怀念的泪水。
相关阅读:
冯涛/又是收麦时
冯涛/我和我的《行吟集》
冯涛/凝望人生
冯涛∕农村娃变石油娃
冯涛∕吹笛子的男人
冯涛∕“鼠”的微诗7首
冯涛∕心怡神畅
冯涛∕十念家乡
冯涛/新生的石油城(外一首)
作者简介:冯涛,系陕西省书协会员、甘肃省庆阳市书协会员,长庆油田书协常务理事长,长期在长庆油田工作。
唐女女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://www.yangtia.com/sjfb/10519.html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