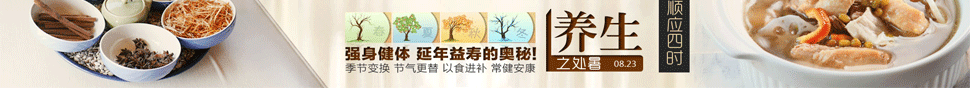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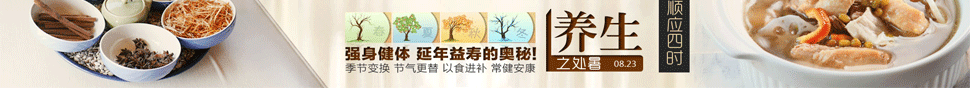
海南南强:是谁改变了百年南洋侨村
摄影|林舒
撰文|杨语
七月上旬,正是海南一年中最热的时候。从美兰机场出来,搭上东线环岛高铁,一路往南开。一个小时后,风景从大片的胡椒、橡胶,逐渐变为稻田、水牛和槟榔,博鳌到了。我们搭上一辆出租车,又钻进树丛里。从资料上看,南强是个小村子,但这里的出租车司机似乎都知道它。新铺的柏油路在太阳下黝黑黝黑,路边成排的小叶桉,零星的台湾相思,羊蹄甲和樟树飞快掠过。驶过一座架在万泉河上的桥,南强村就到了。
南强村有个气派的大门。大门后面,是老村支书莫泽海种的一片黄花梨。往村里走,成排的尖顶,连成长片的青烧砖建成的墙,都在表明,这是个多么典型的琼东农村。
但是,年,碧桂园海南区域南强村美丽乡村项目总监史庆杰初到南强时,却觉得这村子有些破败。居民大多还住在这些建于几十年前、甚至上百年前的房屋里。在雨水多年的侵蚀下,青烧砖,浮雕和屋顶的瓦片已经被腐蚀得黑乎乎的。村里的水泥路也坑坑洼洼。和周边盖了一栋又一栋新的平顶房的农村比,南强村的时间似乎还停留在几十年前。
南强村附近的海岸
晾着的洗净的渔网
南强村面对着万泉河的入海口,三百年前,一群福建移民来到这里定居。他们在近海的土地上种植水稻和地瓜,在山坡上种槟榔,在村里养鸡,在稻田里养鹅。入海口的河水里能捕到俗称“海罗非“鱼,肉质有河鱼的细腻,又有海鱼的鲜和结实。驾船出海,则有无数海产可供捕捞。现在,从村口看出去,是万泉河对岸的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。
像海南的其他农村一样,宗族观念在南强村非常重要。在一户典型的南强人家,正厅正对着大门位置,总有一个香炉供着所有的“公”,也就是祖先。南强人的日常生活,吃饭,会客,孩子玩闹,都在这个香炉下进行。
一栋外墙翻修后老宅的大门,门上贴着玉皇大帝的平安符
一户人家的香炉和牌位
南洋风格的吊灯
一户人家新装修后的正厅,依然是传统性质,香炉摆在“福”字前面
一栋老屋里的正厅
南强村“下南洋“的风潮过后,有不少村民留在东南亚定居,家中祖屋空置。图为一栋被空置的老房子中生锈的门锁
南强人家相连的院子。左侧是独立的正厅和卧室,右侧是每户人家的杂物间和厨房
清末民初,兴起了下南洋的风潮。先是有几户人家到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,开咖啡馆,餐馆,做生意,或者只是打杂工。年,达到顶点。人们合伙坐木船出海,从万泉河出海,沿着海南东部的海岸线航行,之后穿过北部湾,沿着越南的海岸线一路南下。一些人在马来西亚下船,一些人在新加坡下船,剩下的人一直开到印度尼西亚。
在异乡的人没有忘记家里的香炉和祖屋。赚到钱,拍了照片,总要寄回家。陆续有人回家修缮祖屋,把东南亚的元素也加入其中:印尼的花砖,南洋风格的吊灯,外墙色彩鲜艳的浮雕。只是如今风吹雨淋,已经看不出过去的颜色和形态。即使回不来,也要把照片寄给亲戚,挂在自家墙上。
印尼风格的花砖
南洋风格的吊灯
空置房屋中的家具
祖屋意味着归属。年,有一户人家的祖屋被台风刮倒,为了让这家人的后人未来有家可寻,村里人从废墟里捡起材料,帮他们在原址上盖了一间迷你的正厅,放上方桌
多年被雨水侵蚀而难以辨认原貌的浮雕
一户南强人家的厨房,外墙和柱子用青烧砖砌成
南强是为数不多的保存完整的琼东侨村。当地人知道这些老建筑的价值,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对面,在“国际旅游岛”的背景下,它是本土文化和本土特色的代表,也是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。可是村里的年轻人要吃上“旅游饭”,只能到附近的酒店、镇上的餐厅去打工。
莫泽海也是位老华侨。年,为了躲避战乱,他的父亲带着全家人移民到新加坡,在那里扎下了根。五十年代初,海南解放,母亲带着莫泽海回到南强生活,打理祖屋。建设“国际旅游岛”的消息传来,莫泽海也试图带领村民从旅游产业里分一杯羹。他发起村民参股投资农家乐“花梨人家”,名字源于村口的几棵海南黄花梨。骑车环岛的游客大多来这里用餐,也来这里住宿,在假日里更是火爆。但这远远不够,传统建筑的优势没有得到发挥。
南强村老村支书莫泽海在”凤凰客栈“的院子中
从内部看,一户南强人家的大门。大门一般在正厅门的右侧,正厅门正对着下一户人家的后门。门门相连,形成一条风道
年,碧桂园“美丽乡村”的总监史庆杰来到南强。他的任务,是帮助这个村子进行保护性改造,寻找村里保存完好的老房子,改建成民宿、书吧和艺术家工作室,年限到了再交还给村民运营。
这个任务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却不简单。最大的问题,是如何获得当地人的支持。在南强村民的眼里,史庆杰是个“大陆人”。最明显的,从外表来看,他就是个外人。他身材高大,皮肤白净,还不懂说海南话。村民不信任他,村里流传着一种猜测:“他们要骗我们的房子,给了就拿不回来了。”
这时,出手相助的是老村支书莫泽海。
莫泽海的家人大多还在新加坡,他们的祖屋都空着,有些已经破败。同家人沟通后,他把房子交由碧桂园来打造。
两个月后,民宿“凤凰客栈”建起来了,它保留了房屋、庭院原本的结构和建筑材料,连屋内的家具,也是海南农村传统的样式。“凤鸣书吧”也建起来了,不只是游客,村里的孩子们也有了看书的地方。
很多时候,村子似乎没有变。院墙上依然摇曳着三角梅,凤鸣书吧门口的野番石榴树也还在结果,不知从哪个方向吹来的风,带来了槟榔花的味道,熟落在地上的红果子散发出一阵阵香味,和九里香的味道混在一起,构成了村庄的夜晚。
但村子又确实不一样了,坑坑洼洼的水泥路也换成了青烧砖,路面干净,改造好的建筑和旧的建筑立在一起,发出新的吸引力。
夜里的南强村
一栋老宅中内墙的装饰
“凤凰客栈”外墙。这原本是一栋空置、没有屋顶的老房子。修建过程中,残破的青烧砖外墙被保留下来
“凤凰客栈”内部,保留了南强人家正厅的传统样式
新修建的“凤凰公社”
“凤凰客栈”的庭院
“凤凰客栈”一角
村中一角
但村民们的顾虑还没打消,尤其是那些在民宿和书吧工作,以及负责村庄日常清洁的村民。他们觉得,自己成了被管理者,而管理他们的是个空降的大陆人。他们经常当着史庆杰的面说海南话,需要人打扫的时候,就悄悄躲开。
史庆杰很是苦恼。
为了能融入当地,赢得村民的信任,史庆杰颇费了一番努力。一开始,他无法理解村里的生活,习惯了都市的他,觉得这里太悠闲了。每天上午七点左右,村民们起来喂鸡,浇菜,然后就去博鳌镇上吃早餐。早餐有时吃半个小时,有时吃一个上午,可以是一碗粉汤或炒粉,也可以是面包,配一杯加炼乳的红茶、或当地咖啡。这种咖啡也不像他平常看到的,是将咖啡豆磨成粉后,大锅翻炒,最后加入沸水里煮,味道苦而浓烈。村里的阿婆请史庆杰喝自家煮的咖啡,他没加炼乳喝下去,觉得胃被刮洗了一通。
接踵而来的是中午。吃过午饭后,全村都睡了,连蝉都不叫,狗瘫在地板砖上,鸡偶尔“咯哒”一声,比午夜还寂静。到下午四五点,炎热散去,村里又重新热闹起来。各家开始准备晚饭,在附近打工的年轻人也回来了。
史庆杰发现,这里很少有人家单独吃饭。总有个借口,几家人凑到一起吃。今天是这家打到了鱼,明天是那家杀了只鸡,没有借口也可以,随便打个边炉喝啤酒,一喝就喝到晚上12点。
慢慢地,史庆杰也开始睡午觉了。不仅如此,几乎每天晚上,他都去参加村民的聚餐,和不同的年轻人聚在一起。如果没有聚餐,他就去陪阿婆们打海南麻将。
一年多下来,他理解了村民:他们想要的是尊重。从那之后,他再也没有用命令的口气跟手下工作的村民说过话,即使对打扫民宿的阿姨,也是如此。逐渐地,村民也不再把他当外人。村里的阿婆杀了只鸡,会把鸡胸脯留给他的柯基犬。而史庆杰的母亲来探望他的时候,有一户人家把原本留着过中秋节的鹅杀好,送给了他。
来到村里一年后,正值史庆杰的生日,他按照当地的风俗,办了一场流水席。他想,自己吃了一年的“百家饭”,也该回馈一下大家。那天,村里几乎每户都有人到场。他感受到,在这里忙活一年,用自己的尊重换回了别人的尊重。
这一年里,他质疑过很多次,一个年轻人,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一个村子里?一年过去,他才想明白,他正参与的,是一个古老侨村的现代化。
南强村中开小卖部的村民
南强村村民。她的上一辈人在“下南洋”的风潮中到马来西亚谋生,开了一家咖啡馆。现在马来西亚定居,还会定期将照片寄回,挂在祖屋墙上
——完——
题图:南强村村口的万泉河。图片拍摄:林舒
林舒,出生于福建,毕业于集美大学艺术学院油画系,结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,曾任《周末画报》、《城市中国》摄影师。现居北京,自由摄影师,有时候画画。
《行走中国》是界面新闻、正午故事、碧桂园集团及国强公益基金会在今年发起的公益记录项目。我们分别前往广东、广西、甘肃、海南等地,用文字与视频呈现乡村在教育、民俗、建筑等各个层面的故事。
社会剧烈变动,而且将继续变动下去,透过每个故事,《行走中国》关心的是乡村的精神生活,探寻中国乡村的发展,以及我们共同的未来。
《正午7》已上市,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
点击标题再读点儿别的
章宇的黄桃罐头|史里芬和他的魔幻之眼|廉价小旅馆之歌
诺奖得主高锟:与脑退化症抗争的15年|渐冻的家庭,消失的丈夫|东莞工厂里的心理咨询
一个想变成蚯蚓的男人,和想变成鹅的女人|家政工:颠沛流离,家在何处?
四步设置星标,每天正午看正午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