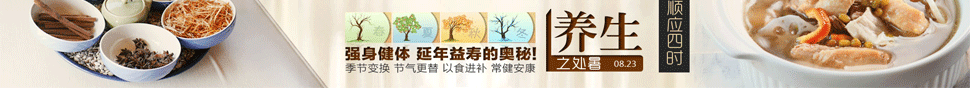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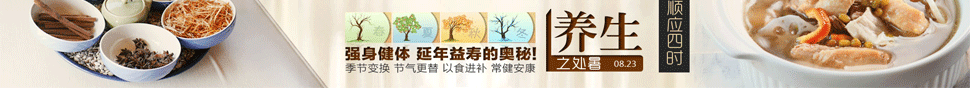
饮食所类,实为繁复。前人著述颇多,予不能追。如宋人林洪,著有《山家清供》;明人李渔,作《闲情偶记》;清人袁枚,撰《随园食单》;清人李化楠、李调元父子,合有《醒园录》。又更如虞宗之《食珍录》、谢讽之《食经》、韦巨源之《烧尾宴食单》、杨晔之《膳夫经》等等……
然上所举,皆为老饕食客,而非手艺匠人,其所著述,未免只谈风雅,有失务实。故而今人仿作种种菜肴,或味道奇诡,或不能安食。至于现当代,有梁实秋先生之谈吃系列、汪夫子之朵颐诸篇,唐鲁孙先生之饮食拾枚,即可驰骋于文章,又能挽袖于庖厨,可谓理论实践两手抓,乃真好食、会食者,食材所属,无以稀贵,只凭心中意趣,往往除朽出秀,请食于客,无不叹矣。
予幼家贫,多事迁移,为求温饱,常穿州过府,十载五易。故黄口能食,遍尝甘苦。凡淮浙之清,中原之酽,蒙疆之犷,两粤之鲜,川湘之蛮,云贵之野,皆略知也。近来肠腑革命,寝不能安,食不能化。正愁容时,忽然兴起,于是弃米就面,午餐则一荤两素,馒头就之;晚膳常用汤面,一指为宽,佐时蔬滑肉,以润枯肠。
如此经月,果见奇效。不免作米面之思,欲有一表,故有此文。
谈谈我所知道的主食。
家山所在,中原旧府。有黄河故道,百里邙山。既是中原,则多植小麦,亦有玉米、豆、番薯、黍(糜子)、蜀黍(即高粱,家乡人谓之蜀黍)等多种作物。如今常见,仅麦、玉米、豆三种,番薯往往自留所种,为副食也。而高粱、糜子,则早无见也。
番薯曾是中原一带劳苦人民的主食,是为粥的主料,豫东皖北一带谓之“红芋糊涂”。“红芋”即番薯,借“红皮芋头”之名,“糊涂”即糊糊,乡音之变,多类于此。近代历史中,中原但有灾荒,番薯则为应饥第一品,番薯常被切片晒干,能存数年之久,煮食即可。后麦产颇丰,番薯欣然让位,小麦登上舞台。
中原吃面,既有无馅如馒头、面条之类,亦有有馅如包子、扁食(饺子)之属,馄饨则不见于餐桌。中原馒头,以为主食,却与南人点心之馒头不同。北人馒头,止于原味,故能佐酱菜;南人馒头,糖霜奶精,恐不能胜于蛋糕。家母籍贯河南,善为面食。每每和面蒸馍,不用发酵粉,只用自家酵头。酵头乃面剂,形如人拳,自然发酵,置于梁头。发面时以刀刮下些许粉末,温水化开,再行和面。母亲和面,亦有其心得。在母亲看来,面的劲道与味道,全在一小撮盐和少量碱面(苏打也)上。
旧时过年,家家户户要于除夕后半夜蒸新馍。竹笼新纱,琼脂白玉,小孩子睡眼沉重,往往听得大人说出锅后,则困意全无,就着咸菜酱豆一口气能啖好几个大馒头。陕西、河北、山东一带馒头均如此类。更有山西、陕北人常于年节嫁娶以花生红枣作花馍,巧手巧剪,其所塑造栩栩如生。盖不再多言。
除过馒头,面条亦是主食。面条,汤饼的后代也。早在两晋便有,唐宋则见于寻常百姓家。宋人笔记中常有提及。宋人黄朝英所作《缃素杂记》有《汤饼》篇,曰:“余谓凡以麪为食具者,皆谓之饼,故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,水瀹而食者呼为汤饼,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。”
余每往一地,则概览其人情,品尝其味道。
河南一地,要说面条,有汤面、捞面、蒸面,凡此三种。
汤面当数烩面,亦有捞面。烩之一字,乃烹饪手法,盖间于炒、炖之间,风味中和醇厚。用之于面,则不能生搬硬套,大抵讲的是其中和醇厚的感觉。烩面所用面条,各地宽窄不一,然多二指宽,不用蓬灰,以盐碱为底,尤为劲道。烩面所用汤水,多是高汤,而高汤首推羊汤,以小羊肉、羊骨(开骨煮髓)共煮,又使中药数味,先大火煮沸,后小火慢煲,至汤色浓白柔和,则成矣。佐以配菜,海带、千张,细细切了作丝;又有香干、鹌鹑蛋;食用时则配香菜、辣椒油。假如配上糖蒜,则味道不可形容也。当然,旧时人家是吃不起这样的烩面的。只是割了二两肉,煮成汤面而已。
捞面,亦是穷苦人家的吃法。面条煮熟捞出过凉,苏子叶烫至断生,用先前备好的蒜汁拌食即可。蒜汁作法,各家不一,常用蒜、盐、酱油,于蒜臼捣为酱汁,也有加入辣椒的。
蒸面,凡豫地,无论东西,皆盛行也。先以豆芽、豆角(豇豆、扁豆均可)、肉片(五花肉为上)、西红柿入锅炒制,及汤汁丰浓,下入面条,宽窄皆可,以手擀面为佳。稍作搅拌,捞出,蒸锅水热,上屉蒸之,待水分稍干,即可食矣。
皖北苏北豫东鲁南一带有一种凉面,佐白醋,盐,黄瓜,芫荽,调制好后,浇一瓢新鲜的井水,即成,风味独特,最适合夏日凉饮。
余五岁上,赴关中。
陕西面食,南北风情各异。关中产麦,好食面。旧时有麦客,一双脚板走东西,一把镰刀割南北,靠力气过活。往往一家麦子割得,除过工钱,主人家必要奉上油泼面,多醋多辣,啖一老碗,力气丰沛。
余父母,无他手艺,为谋生计,惟吃苦耳。在小吃街摆摊,经营一种小吃,曰牛肉酥饼。时至今天,家人偶尔嘴馋,也做一二次,不过饼铛,比不得炭火铁锅,总觉滋味差了一些。牛肉酥饼者,馅饼也。以牛肉碎、大葱,为馅,调味使自家调制五香粉,以油酥起酥。油酥者,滚油泼面粉,搅拌而成。若去关中,不得不食也。
彼时西安城多城中村,各类小吃街多如牛毛,经营者多为外地务工人员。河南人之水煎包胡辣汤,安徽人之牛肉板面,甘肃青海人之拉面。又有关中一带之咸阳汇通面,陕南汉中之面皮米皮、岐山之臊子面。西安本地美食则有各类面食、蒸碗菜、各类泡馍……
余好食麻食。麻食即汤饭,状若小指盖。以豆芽、土豆、番茄、菠菜作汤水,煮食;又偏好荞面饸饹,将饸饹床子架于锅上,将和好的荞麦面放入饸饹床,以杠杆把面挤轧作长条煮入锅中。饸饹亦有高粱面、白面制作的。饸饹,华北西北诸省皆有制作,主料、食料、风味各有千秋。关中水饺,名曰酸汤。最好猪肉莲菜酸汤水饺。莲菜即莲藕,外省人多不能理解如何作饺子馅。莲菜作馅,口感丰富,绵中带脆。
一言以蔽之,关中面食多醋多辣,口感酸爽,食之大汗淋漓,痛呼过瘾。
兰州人的兰州拉面或青海人的兰州拉面。
兰州只有牛肉面,没人叫拉面。除过兰州,内地大多省市之拉面,多为青海人所开。与兰州牛肉面无甚干戈。兰州牛肉面讲究“一清,二白,三红,四绿,五黄”。当然,这是食贩之噱头了。盖每一地每一种美食,大概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,各种文化讲究,各种渊源传统。一个小小的吃食,经过食肆小贩的渲染(或文人编撰)总能攀至某位名人身上。而这名人又常涉及皇帝(所谓御赐食名),各州府大人(所谓穿州过府偶食为惊),或又是文人才子……究竟兰州牛肉面是何滋味,诸君需得去兰州亲尝,起个大早,于兰州河畔食肆面馆中,点上一碗,慢慢品味。盖西北面食与内地面食不同之处,在于和面使用蓬灰。蓬灰者,草木灰也。
自关中到甘宁,不妨一起提了新疆。
新疆自古多民族杂居,饮食上风格多样。类其地貌,盖中国所有之地貌新疆大约齐备。饮食以如此。新疆盛产大米、小麦。传统面食有馕(各民族之馕亦有不同),抓饭(各民族抓饭亦有不同),拉条子(拉面,盖相同也)。
新疆地处内陆,气候干燥,作物一年一熟。凡有三山雪水处,必有两盆米粮川。昼夜之温差,千里之沃野,使得新疆米麦颇为优质。余曾旅居南方,过江淮,大米则两熟,再南,则三熟。米饭也罢,粥水也罢,食之皆不如新疆大米。又有东北大米或宁夏大米,大概与新疆大米相同也。
抓饭。盖手抓之饭也。兄弟民族之抓饭实在是以手抓食,而汉人则惯用勺子(新疆“勺子”是骂人用语,去新疆吃饭切勿说“勺子”)。维族抓饭、哈族抓饭、塔什干抓饭,皆不同也。我在沈阳,与同学同租,常作抓饭。备南瓜、黄红萝卜、羊肉、葡萄干及洋葱。洋葱首先下锅油爆,即下羊肉,稍翻炒,下入南瓜条、萝卜条,继续翻炒,调味,注水或汤,及滚,下入米,水米相持,而后待其煮成熟饭即可。又及,米须提前泡好。
至于拉条子,我本身制作不多,因和面醒面制作颇费功夫。尤以母亲擅长。概不赘述,是一种肉菜混合的拌面。
馕亦不提。刚出锅的馕咸香脆软。有人问何为又脆又软。盖外脆内软也。
北人食面,南人品汤。
余在上海,前后几次赴沪,每次都不忘了吃上一碗面。南京街之熏鱼面、复兴路之大肠面,又有大肉面等其他汤面。上海的面吃的不多,对汤面情有独钟。上海的面不同北方,甚少拉面扯面或抻面,多是机器所制湿面。若吃惯了拉面的北方食客,一时是吃不惯的。盖北人食面、南人喝汤也。上海的汤面,妙在汤中恰到好处的酱油与浇头。老上海人,大多来自宁波。至今上海话还保留着宁波话的诸多特色。如我之“阿拉”,便是宁波话。宁波者,唐之明州也。海上丝路的交易港口之一。与东海与南粤之广州、福建之泉州鼎立相望。宁波面食即多浇头。此处不一一概述。余最爱大肠面。大肠必翻洗干净。大肠面亦可与辣肉面混吃,是大肠辣肉面也。
余到广东,南府之国。食面不多,惟云吞面几回耳。广东之云吞,亦称扁食,然这扁食似更像唐宋时期之扁食,带汤水也。中原地区之扁食已演变为饺子的代名词。广东馄饨,与云吞声相似,故称云吞。广东之云吞又不似南方其他地区的馄饨。比如南京,南京之小馄饨,小而馅少,也是喝汤的。与川渝之抄手,福建之扁食,亦不相同也。广东云吞馅大皮极薄,一口吞,则满口也。口感鲜、香、甜。又与面同煮,谓之云吞面。
写到这儿,饿了,不写了,搞完泡面吃,还要加俩卤蛋一根香肠。
有时间讲讲“野味”。如雕胡饭、槐花饭,蒸榆钱、羊蹄草。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