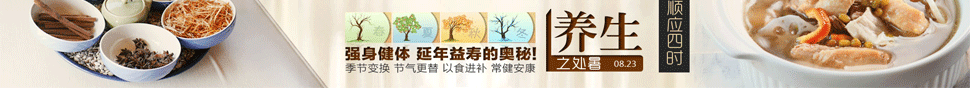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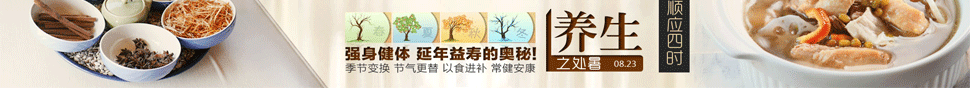
如果没有文明,万仞岗只是散落在姚关境内一座喀斯特地貌的山,如果没有故事,万仞岗再高也只是一面僵硬耸立的石崖,而这一切,只因一句“万仞岗头独举杯”而让历史津津乐道,荡气回肠;而这一切,只因为一颗“姚关人”头骨化石开启文脉,揭开姚关文明八千多年悠久岁月。
大自然造物神奇,衍生钟灵毓秀。万仞岗位于施甸姚关以北,四面群山错落,犄角相望,周围山形奇特,怪状百生。相传明代万历年十一年邓子龙靖边于此,抗缅平乱之后他热衷到处游览姚关名山大川,找寻“洞天福地”。将军儒道兼修,武能金戈铁马扫峰烟,文以豪情壮志咏山河,道可天干北斗定乾坤。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,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,即便是农村妇孺,还是三岁孩童,都能脱口而出一两句“开尔清平记六年,许多盘错破中间.......”。邓子龙在姚关开辟“九引十八洞”,定“三山五岳”,从此火星山为尊,万仞岗为后,一尊一后孕育姚关文明承前启后。
一座山下,总会有几户人家,一眼泉水。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农村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”传统村落的特征,对于万仞岗下的村落而言,占据了天时地利。岗上肥沃的耕地,岗前一片广阔的湿地,当我们追溯村落历史的时候就可以坦言,万仞岗下一定存在过断断续续的人类生活的足迹,就如今岗下的村庄历史随便都是几百年。清平洞《恤忠祠》纪碑里云:“城隍,关庙、五显旗纛诸庙宇,开清平、朝天、万仞诸洞,阅武诸台,火器诸库,报功泉开创皆功也…….”由此可见“万仞岗”为邓子龙所开。它成为了蒜园境内姚关北大门的地标,特别是他那首《九月九日登万仞岗有感》,刻于岗下石壁之上,历经四百多年风雨沧桑依旧鲜亮如新。听古辈老人讲,万仞岗脚下的大汉庄原来叫“莽三坝”,明朝以前就有人居住。相传这里荒无人烟,到处是原始森林,是豺狼虎豹的国度,有一批神秘的部落迁徙到此,首领名为“莽三”,他带着自己的族人在这里进行农耕开发,在万仞岗下取土烧制土陶。“莽三坝”的人们信奉火葬,他们把死者遗体焚烧火化,在腕骨上打上记号,装入土罐,用瓷碗盖住罐口,埋在万仞岗旁。家族式的一代代累积,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火葬墓群。后来莽三坝的后人又相互迁徙,融入了时代演变更迭的浪潮,历史没有记住他们何去何从,但是这一支人遗留下的文明长埋于万仞岗地下,是雷打不脱的事实。由于年代久远,逐渐被后人神话,说他们是会吃人的“老卡辣”,被天收了。新中国成立,土地下户以后,大汉庄村民在万仞岗周边进行山地开凿,期间就经常挖到一些颈长、口小、肚子大约三十多公分高的土罐,村民一致认为这是“老卡辣”的“冷骨尸”,传统观念里这也是不吉利的“鬼老魔”,一经发现,毫不留情的抡起锄头把土罐敲个稀啪烂。随着村落人口的增加,近几年,人口发展出来到万仞岗北侧靠近公路的地方,村民挖地基建盖房屋,四面八方的人涌向这里“考古”,随着挖掘机的开挖,一路路排列整齐有序的土罐刨了出来,重见天日,曾经被村民们认为是“鬼老魔”的东西瞬间成为了颇具价值的古董,一时之间被各大收藏爱好者争相购买。从此以后火葬墓群夷为平地,上面建盖起了漂亮的房子,“莽三坝”家族的火葬墓群彻底消失。
绿水本无忧,青山原不老,不管在这里上演多少故事,延续多少文明,壁立千仞始无名,大地厚重而无言,一切默默的等待,等待着那个势必沿着岁月长河,打马而来的人。边关燃起烽火,时政告急,为保一方水土,邓子龙奉命率三千铁骑,星夜兼程,万里赴戎机,关山度若飞,靖边姚关。“破象阵、斩叛酋、建五关、筑姚城.......”开创了“静观杨柳依依绿,满笑桃花灼灼春”的清平社会,将军百姓爱戴,功垂千古。而面对天子脚下,谗臣忤逆,有时候也会壮志难酬,英雄无奈,而姚关赋有灵性的奇山胜水能拂去心头的寂寞。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。”谁说“将在外,君令有所不受?”为大英雄者,当侧“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。闲暇之余,他打马来到山下,攀崖而上,凌登山顶。将在边关,他平息战乱,整治了内忧外患,收复山河,百姓安居乐业;作为故乡,自己何曾不是一个游子,什么时候能回?极目远眺,只有群山连绵,白云逶迤,不见那手持圣旨的“白衣”到来,只有迢迢阳关道,茫茫烟如织。借问何处是归程?怎奈长亭连短亭…….多么希望这山岗能够有万仞之高,我能“八百里加急”飞跃关山,回到故土。何必在此登凌岗顶,独览众山,自饮自酌,只能与迂回的长风一起,祭奠这片洒满将士鲜血的热土,手中酒,心中情——
关边不见白衣来,万仞岗头独举杯。
西望白云蔽天日,南来震气出楼台。
自怜短发愁残骨,谁说长缨富国才。
何处西风吹铁马,败搂衰草不胜哀。”
万仞岗“开此乾坤”,有了这首荡气回肠的诗刻在石崖上。“虎冠”昭示着后来人“此岗是我开”。这一位可爱的“涂鸦圣手”,他天马行空的浪漫情怀,将如此大气磅礴的名字,毫不吝啬的冠于姚关这座山岗,从此以后“万仞岗”如地脉龙神一般永镇姚关北大门。待邓子龙离开姚关后,万仞岗成为了姚关人缅怀将军的一个去处,多少文人墨客来到这里,膜拜,品读诗歌,与此同时也不忘提笔附上几句“涂鸦”,依附周围,众星捧月,世世代代陪伴。
如果说万仞岗是因为邓子龙靖边而“扬名”,那么它注定因为姚关人而“立万”。年夏天,时任施甸县文管所所长的姚关人乐琪,来到万仞岗研究靖边遗迹,面对文物石刻,作为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敏锐,他问自己,邓子龙喜欢探索姚关的这些崖房洞穴,会不会有更久远的古人在这里生活过呢?人类自古就有在崖璧下生活,洞穴而居的生存本能,他对万仞岗周边环境进行了细致的勘察,希望有更新的发现。他顺崖而寻,当勘察到五十多米开外一个小“崖房”,发现这里隐隐约约有一个洞穴,如果有古人在此生活过,说不定会在洞穴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就是这样一个细心的偶然,一个农民考古的土专家,发现了姚关人头骨化石,把姚关人类发展史石破天惊的向前推进了八千多年。从此“姚关人”挤进了古人类文明发展史中辉煌的的一页,书写了多年的岁月。就像乐琪所说:“发现姚关人头骨化石是我这一辈子考古最大的成就,姚关够古老,自己是一个幸运儿。有些人考古终其一生,不要说完整的头骨化石,就连一小片古人类的指甲壳都不曾发现,这个骄傲足可以让我含笑九泉”。
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,将军在此“开此乾坤”,姚关人在此“唤醒”沉睡了多年的祖先,万仞岗让姚关人找到了根源,万仞岗实属名归——“万仞”之岗,万物之源。
“姚关人”年岁久远,并未走远,他们从洞穴慢慢走了出来,在万仞岗下群居生活,捕湿地之鱼,打山中走兽,茹毛饮血,在万仞岗下进行原始耕作,一代代推动着古老的文明。对于岗下的村庄,有文字记载微乎其微,跨越近五百载春秋,村里的张、杨、吴各个姓氏墓志铭均记载原籍南京应天府。谁才是最早在这里的“本人”,那些“姚关人”到什么地方了呢,灭于猛兽还是死于灾难?还是迁徙到什么地方?是否在人类发展史中“脱节”了,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文明没有断续,前后辗转到了火星山,大崖房等各处如万仞岗一样天生的石崖洞穴当中,随着方圆几里各处史前文明新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掘,从那些石器、陶片、鸟兽鱼虫的骨头化石可以看出,“姚关人”一直都在生生不息,一直都在播种着星星之火,有待着后人的探索,去书写那些散落在岁月时空里的文明。而今,绝大多数姚关人在溯本追源上,认为祖籍是南京应天府,有些的确有据可依,有迹可寻,因为姚关是一个积淀众多文明,经历几次民族大融合的边塞明珠,包罗万象是它的特点和现状。但是这些追溯当中,不乏有人云亦云之辈,和历史的渊源打一点“擦边球”,彰显“归去来兮”。“水自源头树自根”,能够认祖归宗是后世子孙对姚关最大的“孝敬”,首先得从这多年的老祖先拜起,“姚关人”才是这块大地上的根。经过岁月洗涤,历史的激荡,契丹南迁,邓子龙靖边,红白旗演变,滇西抗战.......所有的过往在一起融合成了新社会的姚关人。无论是南京应天府来的,还是南诏遗民,还是因为各种原因来到姚关落地生根的人,都是姚关的一份子,路人终成归人,后世子孙把他们写进了祖先的墓志铭,而“姚关人”墓志铭只有万仞岗才能承载他多年的厚重。
万仞岗左右伴随着两个小村庄——大汉庄和小汉庄,虽然对于“姚关人”而言,它只是短短几百年光阴,却能世代秉承着“开此乾坤”的初心。在这里世代流传着村庄的起源和演变:邓子龙靖边,大破缅寇象阵,《恤忠祠》纪碑云:“火箭中象,象奔,伏弩齐发,红衣数头目俱落象,翼兵冲击,缅大溃……”。邓子龙擒缅象千余烹以享士。民间流传途中有一大一小两头象逃窜,大象在前,小象在后,奔至万仞岗前后被士兵赶上,邓将军起了恻隐之心,就把大象和小象分别留给了村民,从此以后就有了“大象庄”和“小象庄”的由来。在随后一两百年的时间里,随着人口的增多,世世代代在这里居住的汉族人又把它雅化为“大汉庄”和“小汉庄”,也是在名字中寄托一种大汉遗民的归属感。两头象跑过的终点,形成了“大汉庄不大,小汉庄不小”的村庄。对于大、小汉庄的说法,无论是历史的根据还是文学的杜撰,它都不影响万仞岗下人们浓浓的乡愁情怀,都知道几百年以前,这里的青山绿水是多么明透,传统的农耕在万仞岗的黄土地里耕耘,岗下茅舍几间,炊烟袅袅,岗上古木参天,虎啸猿啼,人类发展与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在缓缓上演…….
如今的万仞岗,不再是那个遥远的梦。成为一道恒古的风景。不见了古木参天,岗上岗下均是耕地,村民们热爱土地,就连石头之间巴掌大的间隙都被开凿利用,种成农作物。土地一旁是密集的村庄,住着不同姓氏的姚关子民。公路在岗下穿梭而过,路口立有一块“万仞岗邓子龙题刻”省级文物保护的石碑,顺着路标而上,在三四十米开外,埋着一根写有“文物保护届”的青石界桩,踏过深深浅浅的耕地,路过几堆上了年纪的“土坟冢”,杂乱丛生的荒草中摊出一股小路,两边开满了鞍叶羊蹄甲,万仞岗下崖房刀削,隐约成钟乳状,崖中镶嵌着如蜂巢般的“洞”,而这些“洞”又相互叠加成极具喀斯特风貌的石崖,岁月的鞭打凸显着沧桑,是一种看不到开头,望不到结尾的宇宙洪荒。地锦牵藤附崖,滋生绿鳞般的叶子,络石树根挂璧,裸露在外,在手巴掌大的绿叶间打着紫中带粉的苞,这仅有的绿,把无欲则刚的石壁加了一点岁月的温柔。七八丈高的崖子上有一个大窟窿,如一只深馅的眼眶,深邃的天眼,洞察着一切缘生缘灭。洞口被磨得光滑,一边陡峭的坡上,辟出一道单脚掌可以攀爬进去洞里,挂在半空的小径。小时候和伙伴有过爬进去洞里的经历,黑乎乎的一片,只听见蝙蝠在黑暗中叽叽的叫声,不时煽动着翅膀,如黑暗中的幽灵,洞口下依稀可见隐隐约约的“幽谷”二字......时过境迁,如今想起浑身鸡皮疙瘩,看见小径就让人不寒而栗。不变的是邓子龙的诗词早已融入了万仞岗,在石壁上“不朽”,任凭岁月斑驳,总有好心人会用红漆把它勾勒鲜艳,供世人缅怀。“开此乾坤”已经模糊,很难想象当时这个“涂鸦达人”是借助什么雕刻上去的,难道将军自有神力,即使提壶进洞当如履平地。抬头仰望,突兀绝伦的万仞岗与蔚蓝的天空自成一体,犹如巨石冲破水中天,蓬松的白云是它翻江倒海的浪花。
也许是邓子龙的光芒更甚,从一定程度上掩盖了“姚关人”遗址,很多人都认为“姚关人”遗址,就是邓子龙石刻之处。或许是它年代久远,久远到人们的自信浓缩成了一句落实在口头上的广告词——我们姚关有深厚的文化底蕴,万仞岗出土了多年前的姚关人头骨化石!万仞岗姚关人的遗址如不起眼的灰姑娘,默默的躲在一旁,伴随四季轮回,岗头的草木摇摇欲坠,凌乱萧条,和僵硬的石壁风化成为一个模糊的印记,即使有个“万仞岗遗址”的市级文物保护墓碑,也是微不足道。村民们在左右种植了两篷竹子,耕耘着“姚关人”曾经耕耘过的黄土地,才让这个古老的岁月弥漫着一点烟火气。
踏着一垄垄黄土地,翻过高高矮矮裸露在外,被岁月雕琢得千疮百孔越发坚硬的顽石,终于登上了万仞岗顶,山顶宽广平坦,黄土地被耕耘得金光闪闪,偶尔也会有一两个褐色的石头,宛如荒古岁月里遗落于此的石兽。这里丝毫没有岗的味道,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脊梁给人舒心踏实,行走在这里,头顶的烈日骄阳在微风中多了一丝温柔,心旷神怡,四面群山奔来眼底,村落一览无余,田园如绸,湖水如镜,行人如蚁在忙忙碌碌,车辆如鱼自由穿梭,真是一览众山小,山高人为峰。那些散落在时空里的故事浮过脑海,是谁堵住了鱼洞山“万鱼归湖”?是谁斩断了象鼻山导致“一象短鼻千象回”?是谁叫醒了天鸡让“仙鹤煲蛋”遗留人间?是谁戏了金蟾?而让它等了千年万年成为一只丑陋的蛤蟆.......每一座山都有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传说,而这些传说都伴随着山在万仞岗面前萦绕.......萦绕........
时光在这里穿越,沿着岁月一路走来的历史长河,我看到了“姚关人”三五成群的来到过这里,披着兽皮,持石刀石斧,相互吆喝,在追日逐鹿……邓将军又来到岗头,手持酒杯,对着姚关大地,一饮而尽,所有的豪迈,所有的惆怅,所有的期盼,所有的所有…..一饮而尽。
时间轮回,岁月变迁,就让你我再一次登上万仞岗,寻根“姚关人”,追忆邓将军,万仞岗头再举杯!不为边关“白衣”,只为此生有幸为姚关人。曾经思念翻越江海,今天亦可手眼通天,万仞岗下谱写新的蓝图,高速公路穿山过崖,横空出世,碧藕红莲锦绣河山,今再次举杯,不望归途,只为起航。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

